编者按: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是指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人员。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既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由于各种消极因素和不良环境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情况日渐突出,给社会、家庭和个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感化、教育工作也显得刻不容缓。
从2006年开始,我省推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10年的时间,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地预防、控制了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同时切实地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普通社区矫正不同,因成长环境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因素,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更需要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耐心地进行工作。我省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上有着许多特殊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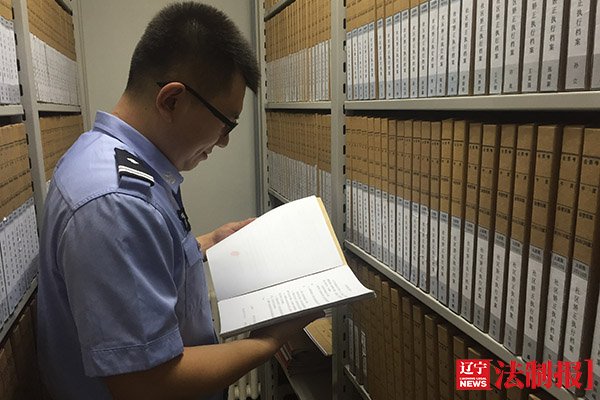
每一名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都有自己的档案
【背景】
“破损家庭”引发
未成年人犯罪最多
进入本世纪,我省青少年犯罪状况虽然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未成年人犯罪率却逐年攀升。
2004年至2006年3年的时间,我省青少年犯罪类别就发生了重要变化,杀人、伤害、强奸、绑架等暴力案件突出,涉案达到9039人,占全部青少年犯罪总数的46%。
通过数据分析,青少年犯罪中曾犯过罪的人员少,多是因一时冲动造成“激情”犯罪,而这些与青少年受教育程度很有关。
值得重视的是,在全部未成年服刑人员中,认为家庭不温暖的所占比重最多,占45.9%。阜新市抓获的一个流氓犯罪团伙,其中13名未成年少女均来自“破损家庭”。
而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将其与社会隔绝进行教育改造,不仅难以使未成年人形成完整的、健康的人格,而且由于长期不与社会互动,在刑满释放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融入社会,增加了再犯罪率。
所以,2006年,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运而生。
虽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乏社区矫正的共性,但更有区别于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者因家庭环境、成长背景、性格特征、犯罪原因均存在不同之处,其矫正措施不应该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呈现出来的各种特点,社区矫正工作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转化、改造要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以矫正其不良的心理和行为。
而若想因材施“矫”,首先就应该对每一个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社会调查,确定其犯罪原因,为下一步量身定制一套个性化的未成年人的矫正措施提供依据。由于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成人化的特点,通过对其成长经历、社会关系、犯罪原因等进行全面调查,能更深入、更客观地探求犯罪根源,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矫正,使之顺利回归社会。
其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应重视心理辅导。未成年人因心智不成熟,世界观尚未定型、人生观显著错位、价值观严重扭曲,才会误入歧途,走向犯罪。所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要依托社区矫正心理咨询室,使他们彻底告别过去的不良生活方式。如为新入矫的未成年犯进行心理测试,可以全面了解未成年矫正人员的心理特点,准确、直观、科学地反映其悔罪态度,并作为进一步开展心理矫治的数据依据。
【措施】
成功解矫是一场艰难蜕变
个性矫正去除标签
杜磊(化名)之前是沈阳市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的一名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从最开始的不听管教到成功解矫,杜磊的身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杜磊最开始并不住在和平区,而是住在新民,杜磊的父亲忙于工作,并没有太多时间管他,一次吵架后,杜磊就离家出走来到了和平区。
父亲找了他3个多月,才终于在和平区找到了杜磊,但杜磊也已脱管3个多月,原司法所表示不愿意再接管,不得已,杜磊父亲带着杜磊找到了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
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科长曲岩了解情况后,同原司法所沟通,愿意接管杜磊,但前提是杜磊必须在和平区管辖范围内居住。
为了让孩子能够再次接受社区矫正,杜磊的父亲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给杜磊租了一间房子。
面对叛逆不听话的杜磊,曲岩耐心地给他讲解法律法规,并根据他的情况为他制定了矫正计划。曲岩说:“我们了解到,杜磊的父母已经离异,杜磊跟着父亲过,但父亲经常去外地打工,根本没有时间管他。现在杜磊在跟着和平区一个亲戚打工,我们觉得让他学一门手艺不是坏事,于是给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社区矫正计划,比如周一到周五必须认真工作,周末还要学习法律知识,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等等。”
在曲岩的耐心劝导下,杜磊认真按照矫正计划执行,最终顺利地解矫了。
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根据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背景、文化水平、兴趣爱好、心理状况、犯罪事实等,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个性化矫正方案,并通过跟踪了解走访,与其家庭、学校、朋友沟通联系,收集评估矫正效果,适时调整矫正方案。
和平区人民法院派驻到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的法官郑迎丽告诉记者,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有几点:“通过我们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未成年犯罪原因一般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因素。往往表现为自暴自弃、自制力差或者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拉帮结伙,为了‘哥们义气’而犯罪;二是家庭因素。未成年服刑人员中,离异家庭导致家庭教育缺失,过分溺爱导致教育方式不得当;三是学校因素。部分学校依然以‘考试分数’来衡量一个学生的好坏,针对一些‘问题少年’或‘垫底差生’的不良行为不闻不问,导致其厌学逃学。”
针对上述问题成因,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社区矫正工作者会鼓励未成年服刑人员自己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矫正计划,以引导为主,循循善诱,鼓励每次取得的点滴进步,进而帮助其增强自我约束的控制能力,来改善自己的行为。
同时,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还联合法院少年庭法官、所在社区干事、社会志愿者对未成年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和定期督促,并对改善周边居住环境,降低与不良朋友接触程度提出适当建议。
曲岩说,在个案矫正中,既要让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认识到犯错就得接受惩罚,不能以“一时冲动”“哥们儿义气”作为触犯法律的理由,更要努力做到去除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身上的污点标签,减少社会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身份歧视。反复引导,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平区未成年人入矫仪式现场
创新矫正注重再社会化
2012年的6月,鞍山市的闫明明(化名)前来辽阳市弓长岭区社区矫正团山中队报到,闫明明的妈妈也陪着她。
团山中队接待了这对母女,向闫明明进行入矫教育及社区服刑人员须知后,腼腆稚气的闫明明却哭了。
闫明明的母亲说,孩子本不想来报到,怕磕碜。
团山中队工作人员看了其犯罪事实后说:“你的犯罪也是因为不懂法造成的后果,在抢劫过程中抢到50元钱,并不认为构成犯罪,但事实已经犯罪了,就要承担责任。但我国司法实现过程中,出于对未成年保护,中队采取错峰报到,既由监护人陪同,单独报到,又不脱离监管教育,同时尊重保护了未成年。”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闫明明情绪好转了很多,敢于勇敢直面社区矫正了。
随后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团山中队对闫明明在内的几名未成年采取单独与成年服刑人员隔离的方式,从网上下载一些与法律相关的内容让他们反复阅读,有不懂的地方请教专家进行解答,同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
2014年4月的一天,闫明明拿着一张招工表来到中队,上面有一栏是否有前科违纪行为,团山中队来到用人单位与其单位负责人进行沟通,并拿出相关文件对闫明明在中队社区期间的优秀表现给予全面鉴定,希望用人单位能够给她一次机会。用人单位经过全面考虑终于破格录取为合同制人员。
闫明明在社区矫正解除时,为了感谢团山中队的工作人员还送来了红包,但是被团山中队的工作人员婉言谢绝了,大家都说,什么都没有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更让他们开心。
在随后的回访中,团山中队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闫明明现在已经成家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组成了家庭。
正是团山中队创新的社区矫正方法,才让闫明明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并且重回社会。
在沈阳市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记者也看见了创新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式。
曲岩告诉记者,和平区司法局2015年6月在全市率先开通了“和平矫正”微信服务号,面向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法制教育、矫正帮扶宣传。该服务号设置专栏。
其中,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坚持寓教于乐,向未成年服刑人员传播易懂、有趣的“你身边的法律知识”、“假期打工骗术揭秘”、“保护自己,做懂法少年”等有关专题普法信息推送,促使他们真正认罪悔过、修身养性,形成正确的行为规范。
此外,和平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法庭也创建了“少年法庭陪审团”微信群、“和平法院少年法苑”QQ群,同时还创建了微信公共号“少年法苑”,将互联网引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
和平区目前有30名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除了少数没有智能手机的社区矫正人员家长外,大部分家长关注了微信“少年法苑”,微信“少年法苑”不仅经常发布典型案例和教育子女知识,进行普法宣传,同时根据家长的反馈和请求及时对矫正人员进行帮教。
教育矫正回报社会
白超(化名)今年16岁,是沈阳市和平区司法局南市场司法所的一名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2015年8月入矫。但是刚入矫的前2个月,白超根本不听管教,从来不按时报到,甚至不接电话。不得已,南市场司法所把此事汇报给了曲岩。
曲岩了解了此事,第一时间找到了白超的父母。
经了解,原来白超的父母平时都忙于工作,根本没时间管他,也不了解社区矫正是什么,觉得孩子回家了就行了。
于是,曲岩就把白超和他的父母一起请到了沈阳市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曲岩和郑迎丽就什么是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有什么意义、如果脱管会造成什么后果等问题,向白超和他的父母进行了解答和说明。郑迎丽说:“社区矫正,是一次重新改过的机会,如果一开始不当回事,不珍惜这个机会,以为判完就完事了,那就彻底失去了社区矫正的意义。严重了还会被收监。”
经过这次谈话,白超和父母都明白了社区矫正的意义和重要性。白超的父母表示,以后无论工作多忙,都一定按时报到,积极参加社区矫正的所有活动。
曲岩说:“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和普通社区矫正人员不一样,因为在加强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教育的同时,还应该增强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的法律知识。所以我们经常组织一些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和其监护人的法律培训,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社区矫正的重要性。”
在教育改造的同时,和平区社区矫正管理教育中心还坚持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关系。
曲岩说:“和平区各司法所与所在街道、社区还建立了‘社区公益劳动服务基地’,司法所定期组织服刑人员对社区楼道、花园等进行卫生清扫。针对部分在校未成年服刑人员,在尽量不打扰学习的前提下,安排其在周末、寒暑假等时间进行劳动,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关爱和帮助,教育他们做一个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益的合格守法公民。”
【他山之石】
江苏常州:聘用“人生导师”帮助走出歧途
2015年10月,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钟楼区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联动互动,就保护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健康成长,集法治教育、犯罪查处、专门审判、社区矫正于一体的系统化管理模式正式成立,此举为江苏省首创。
钟楼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心借助钟楼区社区矫正机构——“清心驿站”的平台优势,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打造适合未成年人矫正、管理、教育场所,提升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的工作成效。
此外,钟楼区社区矫正中心还和左岸——常州公益助学联合会联合开展了“迷途中的灯塔”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帮扶服务项目,为钟楼区9名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每人聘用了一名“人生导师”,在矫正期间监管,并从各方面帮助他们从“失足”中走出来,面对以后的人生。
据了解,9名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是初中、中专文化水平,文化水平和认知都较低,对一些问题缺少正确引导,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问题导致其性格及心理层面的不健全。而这9名“人生导师”均是具有较高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社会人士,来自学校、检察院、医学会、地方文化研究会、心理学会等。
9名“人生导师”已经充分了解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工作学习以及社区矫正等情况,他们将每月至少与孩子们进行一次交流谈心,并建立工作笔记,根据受导者成长过程中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对症下药,制订受导者的改进和发展目标并指导其完成,而且定期到受导者家中进行家访,帮助和指导家长改进家庭教育方法。
【延伸】
减少“校园暴力”的
刑事责任年龄交锋
我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连年下降,却呈低龄化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5年,我省法院判处未成年占判处总数的4%,共同犯罪案件占总数的25.45%,总数和比例逐年下降。
其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占总数的10.77%,2013年以来,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占比例呈逐年小幅上升趋势,2014年达到11.36%。
同时,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和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案件也受到普遍关注。
于是,有观点认为应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对于是否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正方”观点认为,校园暴力已严重到了一定程度,那些低龄的未成年施暴者,如果不能得到有力的管教,会给社会带来更大危害,法律必须正视并解决相关问题。而“反方”则认为,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合适恰当的,不能意气用事,盲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反方”观点认为,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以及“校园暴力”事件频发,这些不仅是未成年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未成年人暴力呈现上升趋势,恶劣性逐渐加重。如果只一味强调打击,忽略了社会环境的改善,恐怕很难真正扭转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趋势。
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更多的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犯罪的预防,多是正面保护措施,缺少惩戒性规定。低龄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其解决还需要综合施策,而最为重要的是出台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规,恢复并健全相关矫正制度。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工作由于专业工作人员缺乏,经费保障措施不到位,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因此,采取必要措施强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势在必行。
